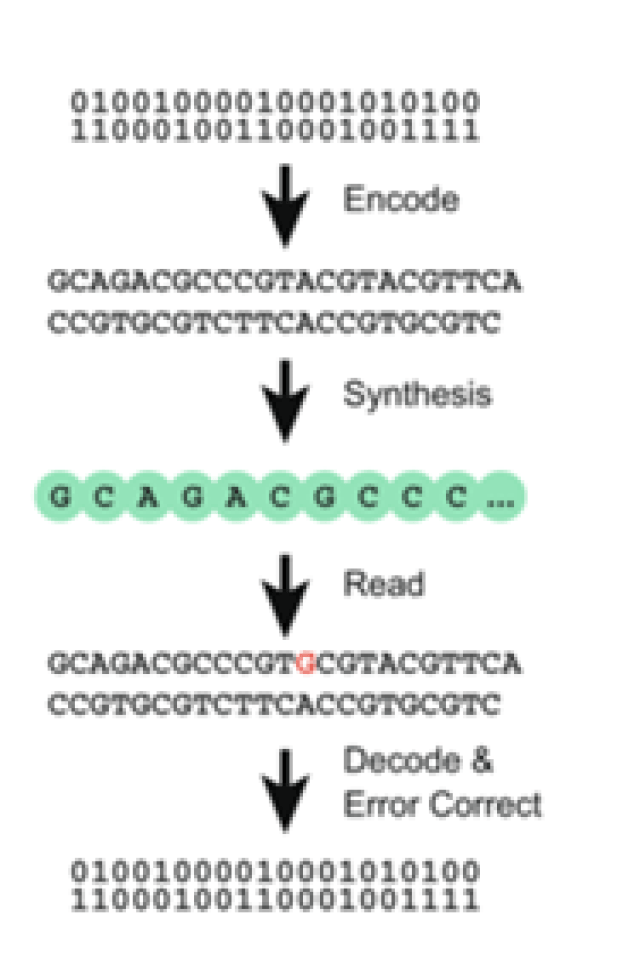
一份来自香港的法院冻结令,让娃哈哈340亿的遗产争夺战彻底公开。三个陌生的名字,一场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家的战争。
娃哈哈帝国的继承权,最后变成了一道血缘鉴定题和一道法律选择题,但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。
故事要从2025年7月的那个下午说起。一张正式的法律文书,贴在了宗馥莉的办公室门上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商业文件,而是一份来自香港高等法院的资产冻结令。冻结令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名字,但这些名字,在娃哈哈的公开世界里,从未出现过。
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炸开的。三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人,自称是宗庆后的子女,要求分割遗产。这场跨境的财产争夺,让所有商业剧本都显得平淡无奇。问题的核心,在于一个设立在海外的家族信托。
宗馥莉一方坚称对此毫不知情。但对方直接甩出了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离岸信托文件,白纸黑字,签名齐全。这些文件像幽灵一样凭空出现,动摇了宗馥莉作为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根基。只看文件,香港法院很难不支持原告的申请。
为什么原告选择在香港发起诉讼?因为香港的法律体系,对信托文件的承认度非常高。只要文件在程序上没有明显瑕疵,法院就会倾向于认定其有效性。这是一个精心选择的战场,目的就是用法律文件本身,来对抗宗馥莉在内地的绝对优势。
这个人叫杜建英。在娃哈哈的老员工记忆里,她是“杜阿姨”。当年宗馥莉14岁独自去美国读书,就是这位杜阿姨一路护送。她曾是公司的党委副书记,一个看起来退居二线很久的人物。但现在,她成了对方阵营里最关键的军师。
这个消息传出时,很多人才反应过来,这位“杜阿姨”可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。九十年代娃哈哈在全国扩张,布局重庆、陕西这些核心生产基地的时候,背后就有她的身影。她对公司的了解,不只停留在生产和管理层面,更深入到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角落。
根据内地的继承法,血缘关系是继承权的最基本前提。没有血缘关系,再完善的法律文件也可能面临挑战。反过来,一旦DNA鉴定证实了血缘关系,那么无论有没有出现在信托文件里,这三个突然出现的“弟弟妹妹”都有权要求分割遗产。
同一个父亲的血脉,在深圳河的两岸,被放进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计算公式里。这让整场官司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迷宫。宗馥莉的律师团队必须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,一个要证明文件的无效,另一个要应对血缘关系的挑战。任何一个战场的失利,都可能导致全局的崩盘。
这个沉默的角色,是杭州市上城区国有资本运营集团。它不是一个小角色,它手里握着娃哈哈42。2%的股份,是除了宗氏家族之外最大的单一股东。在如此剧烈的控制权斗争中,这个大股东却选择了“隐身”,既不表态支持宗馥莉,也不对挑战者发表任何看法。
为什么它会沉默?答案很简单,坐山观虎斗是最好的策略。家族内斗越是激烈,对国资就越有利。旷日持久的跨境官司,会耗费掉宗氏家族大量的现金和精力。等到双方两败俱伤,公司价值可能出现波动,管理层可能陷入混乱,到那个时候,国资再出手,无论是为了稳定局势还是为了谋求更大的控制权,都将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好的时机。
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这场争斗的核心。那笔21亿美元的信托资金虽然巨大,但它更像是一个开胃菜,一个用来撬动全局的杠杆。
这部分股权是宗庆后个人名下的资产。一旦内地的法院根据DNA结果,判定三个私生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,那么这29。4%的股权将被一分为四。这意味着,宗馥莉个人能够继承到的部分,将从29。4%骤降到7。35%。
这个数字的变化是致命的。加上她原来持有的股份,她的总持股比例也将被大幅稀释,可能会失去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。一个商业帝国,可能就因为一场家庭内部的战争而分崩离析。
股权一旦被分散,娃哈哈这家巨型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,将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。这或许才是杭州国资最希望看到,也最需要介入的局面。
这笔钱的用途,据说是当年为了规避某些税收,通过一个海外的离岸账户进行的。在公司正常运营的时期,这种操作可能并不罕见。但在遗产争夺战的背景下,这笔钱的性质就变了。
它成了一个可以被大做文章的疑点。对手的律师可以把它描绘成一次非法的资产转移,甚至与更严重的“洗钱”联系起来。这不仅会给宗馥莉带来法律上的麻烦,更会在道德和信誉上对BG大游她造成打击。一个原本为了省钱的财务安排,现在变成了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证据。
这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,其实已经没有赢家了。官司烧掉的钱,足以新建一条完整的饮料生产线。而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,一旦破碎,就再也无法复原。娃哈哈的未来,已经和这起官司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,充满了迷雾。